


我亲爱的大小姐
我一直想写写大小姐的故事,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大小姐已经离开人世很多年。她在世的时候,我还是一个刚入学的小屁孩。印象中,她每天都很严肃,从来不笑,她的头发永远都是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,盘成一个小小的髻,那髻上罩着黑色的纱网。她爱穿素色暗花的斜襟小袄,左边别着一块小小的手帕,讲话时偶尔把手帕取下来拿在手中,微微摇来荡去,配着一贯高高在上的语气,说到动情处,她还会把手绢举过脸颊,在额头眉眼周围轻轻擦拭着。
那时我总会很纳闷:她在擦什么呢?没见她淌大鼻涕呀。
大小姐个头不高,听说年轻的时候就很瘦弱,如今更缩了水,显得瘦骨伶仃,所以走起路来非常快,如一阵小风。我们家人待她极好,有一次接她来我家小住,派我陪她遛弯。遛弯就遛弯吧,小孩子可不懂遛弯还要守啥规矩,我当然蹦蹦跳跳,很快就跑到了大小姐前面。这可不得了,后面的大小姐居然冲着我过来了,一溜烟儿似的又赶到了我前面,也就是几步远。她这样的举动让我心头直痒痒,我咧嘴一笑,准备冲上去和她赛一赛。腿还没蹬地,大小姐就回过头来,淡淡地说道:“后面跟着。”
听到了吩咐,我一下子僵在原地,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她是闹哪样啊?见我一时反应不过来,前方的她放慢了步伐,身子左右轻摇,刚才的那阵小风不见了。长大后我回想起来,那款款而行的背影,竟有点民国淑女的优雅,完全不像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。我毕竟脑瓜转得快,才不管她怎么吩咐,更不服气被一个老太太抢先,还要跟在她后面慢慢扭啊扭的,便又一溜小跑冲上前去超过她。大小姐不甘示弱,依旧一阵小风超过了我。就这样我俩你追我赶,弄得满头大汗。我一屁股坐在路边小卖店门口的小马扎上,怎么也不肯走了。大小姐却缓缓落座于旁边高我一截的长椅上,取下手帕轻拭汗水,然后咯咯一笑。我转头看她,发现真是神奇,她可以只发出笑声,而脸上的严肃表情没有一丝变化。
毕竟年纪大了,这段路的剧烈运动还是把大小姐累坏了,但她没有上气不接下气,只是微微喘着,喊老板开一瓶橙汁汽水。她问都没问我,看都没看我,就自个儿微微仰起头,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了起来。看着她喝汽水,我只能干着急。愤怒之下,我的脸更红了,脑门上憋出了丝丝白气,汗水一滴滴落下来。多年后,更神奇的记忆也浮现出来,因为看到了更为神奇的场景,我随即傻眼,大惑不解——她竟可以把每口饮下的量控制得如此均匀,看起来不像在喝汽水,而是像在款待客人时品鉴着等的红茶或红酒那样。我才明白,这个长辈在自然得体地吃独食,全然不顾那个饥渴的小孩。
这么端庄这么有范儿,像是个地主家的大小姐。半瓶汽水喝下去,大小姐呼吸恢复了平顺。她缓缓地把剩下的小半瓶汽水递到我面前,神情淡淡的,没说一句话。本来看她喝汽水就嗓子冒烟的我委屈地接了过来,因为实在太渴,兜里又没钱再买一瓶,我咕嘟嘟一口气喝了下去,心里的火却更大了:大小姐,真会欺负人啊!
回到家,我“哇哇”地哭了一下午,轮流向每一位家人抱怨了一遍大小姐有多么的讨厌,多么的自以为是,居然和我这个小朋友抢路走,抢汽水喝,像个地主家的小姐,人人都得围着她转。姥爷听后没哄我,哈哈大笑,摸着我的头说:“别气别气,知道不?她还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小姐。所谓大小姐,就是不用劳动,从小有十几个丫鬟伺候着,
好吃的好喝的,要啥有啥。 ”
听了姥爷的话,我懂了,大小姐就是支使别人干活,让别人伺候自己,自己不动手的人。别人不能走在她前面,得跟在后面;更不能抢在她前面吃喝,得先让她享用才行。这时,我幼小的心里竟突然生出了一丝莫名的快意,在我纷繁的童年记忆中,那是次感受到了阶级平等的优越性——优越就优越在大街上我想跑到前面就跑到前面,不用听命于大小姐跟随其后;渴了想先喝汽水就先喝汽水,不用看着大小姐解渴而自己嗓子直冒烟。可是,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,旧社会早就翻篇了,大小姐倒好,怎么还把自己当成众人捧着的大小姐呢?
刚刚说到,大小姐的表情一向是比较严肃的,几乎不笑。她的面容美丽,却一直笼罩着哀愁。
在我的印象中,她分明曾破天荒地笑过三次。她笑起来的样子早已记不太清,等我长大,了解了大小姐的悲欢人生后,想起了她的笑,才惊觉自己是多么的狭隘,只看到表象,只想到自己,却不曾体谅过她的感受。她的怪异和疏离的背后,也许是沉重的命运之痛。我不由得有些愧疚,甚至想对大小姐说声对不起,想让她原谅我的童言无忌。
假如生命可以重来,我一定要对大小姐郑重地说:日子过得那么苦,您就多笑一笑吧;既然生活已经用年轮镌刻了我们每个人的样子,让我们的手无力再去改变,不如我们就放开怀抱吧。
次是家里来了远方亲戚。大小姐端坐在高高的炕沿上,垂头看着对面矮沙发上溜边歪坐着的山东老奶奶,讲起自己儿时家里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金银珠宝;讲起日本鬼子打来时,全家逃难把所有的金元宝都埋在了自家宅院门前的桂树下;讲起那些元宝多么的有分量,闪着多亮多亮的金光。然后,大小姐笑了,脸上写满了回味与满足。
站在一旁的我才不信她说的,一撇嘴,嘀咕着:“真贪财哦。”
第二次,妈妈拉着我一起给大小姐送去中秋的吃食。一开门,她竟已笑眯眯地守在门口。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遭!要知道,以前任何一次 “拜见 ”,她都只是一个眼神使唤小保姆去开门,自己则稳稳地坐在炕沿,见到来客,扬起脖子缓缓地问一句:“来了?”
这十分罕见的守候和笑容,弄得我们母子俩不知所措。大小姐不说话,我们更是万分紧张。慌乱中,谁也没注意到大小姐剪了新发型,没有了盘在脑后的发髻,取而代之的是齐耳的短发,看起来像是老年版的刘胡兰。现在回想起来,她那么迫不及待地站在门口,一定是想让我们对她的新发型赞不绝口吧,至少也要客套恭维几句,但出乎意料,我们竟跟啥也没发现似的,就低头进了屋,害她空欢喜了一场。还是没说一句话,她收起了笑容,缓缓地随我们进了屋,又缓缓地坐回炕沿,立刻恢复了严肃的表情。
后一次,那时候她身体大概已经不太好,妈妈把她接到我家照顾。她倚靠着床边柜,已经不怎么再有高高在上的姿态,只是用手绢捂着嘴巴,轻轻地咳着。旁边大床上,我和几个小伙伴正披着床单,拿着手电筒和大折扇,举行“盛夏消暑演唱会”。我们群魔乱舞抱成一团,喊破嗓子的歌声震天响。
大小姐看着我们表演,歌唱,突然呵呵呵笑了起来。
那天她很虚弱,却笑了很久,后来甚至想努力举起手来鼓鼓掌。看到她笑了,我又一次不知所措,停下了乱唱乱跳。回想起来,她笑起来竟有一双好看的弯月般的眼睛。如今细细思量,她还真有些 “大小姐”应有的气韵,哪怕她已经挺不直腰背。命运又是如何对待她的,使得她如此孤独,如此隔绝,连笑一笑都如此难得?我隐隐觉得,大小姐的内心深处一定有许多故事从未与人言说,关于身世,关于来路,关于梦想的实现与破灭,关于个人与时代的“分分合合”。
那时的我逐渐对大小姐有些好奇有些想接近,但没等我升入初中,大小姐就去世了,我的探寻落了空。近二十年时光,常与身边的朋友们谈天说地,但从未提及过大小姐,大小姐的样子我也早已记不真切了。
2015年,一次出差,我要去一个位于长白山脚下的自然村落考察。与姥爷的电话中,得知那小村庄正是大小姐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,姥爷也出生在那里。我便安排姥爷从南方飞回东北,旧地重游。
那是一座景色秀丽的村庄,高大的白桦树参天而立,白云在空中静静游动。天色那么的高远澄澈,空气中散发着淳朴的气息。
姥爷看着眼前的一切,红了眼圈,他说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整个家族从山东到东北的全部记忆,特别是大小姐的。于是,在那个夏日,坐在大小姐曾住过的两间木瓦房前,姥爷抽着老乡给他卷的旱烟,讲起了大小姐的身世过往。
1925年,大小姐出生于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大户人家。大家长即大小姐的爷爷是远近闻名的中医,家中宅邸上百间,耕地上千亩,长工丫鬟近百人。大小姐是家中长子的个孩子,她生来俊俏,声音清脆悦耳,又爱笑,很招爷爷疼爱。全家上下都金贵她,追在她身后,喊她“大小姐”。
大家族有很多规矩,比如全家人都要等到大家长用餐完毕才能上桌吃饭。大小姐是个例外,想吃时就爬上爷爷的腿,拽拽爷爷的羊角胡,爷爷便笑眯眯地喂她好吃的。
日后的大小姐总能一遍又一遍地记起坐在爷爷腿上吃饭的场景,好像刻在心上一样清晰:烛火在桌边投下温暖的影子,摇摇曳曳,全家人都候在门外轻声细语,爷爷还会偷偷用筷子沾一滴酒给她喝。
爷爷还喜欢把一些金银小物件塞到大小姐手里,但大小姐一点都不喜欢。她觉得穿金戴银拖拉麻烦,根本比不上坐在自家宽阔的月台上,听曲乐班子合奏一曲《关里夜》。大小姐喜欢跟着那曲子咿咿呀呀地哼着,稚嫩的童声好听,粉琢般的脸蛋上笑容动人。
就这样,大小姐学会了很多曲子,每天唱的都不重样。大小姐仗着爷爷宠爱,脾气难免有些骄纵。她不爱听私塾先生念书,只爱唱曲子。先生摇头,拿她没办法,父母只能叹息随她去。
一晃到了1937年,大小姐12岁。那年除夕夜,冰天雪地,寒风吹得人骨头都疼,竟下起一场大雨。将大小姐视若珍宝的父亲惹上了急病,猝然身故,只留下了孤儿寡母。可怜妇孺遭人欺。大小姐的叔叔家和她们家有一块界石,叔叔经常在半夜偷偷地把界石推得更远,占据更多的地盘。爷爷虽然看不下眼管过一次,但防不住儿子总这样。后来,爷爷得了大病,更无力出手阻止叔叔对大小姐一家的欺凌。爷爷也很快去世了,叔叔自然成了家长,对待嫂子更加冷面冷心,没说什么就分了家,把嫂子的小院挤成了一小间,留下了不多的钱财和两个丫鬟。大小姐的母亲带着她和妹妹,境况凄凉可想而知。因为发不出工钱,大小姐的母亲把丫鬟们全打发走了,开始是卖大小姐的金银小物件,后来是卖自己的首饰。生活只有辛苦。
大小姐真是天真烂漫,从小没有受过裹脚之苦的她到处跑到处玩,一点也感受不到人世之艰。雨中过除夕,她觉得很有趣,不管雨大风急,不听母亲的连声呼喊,不怕冻坏身子,就跑到院子里踩水,笑着唱起歌来。她不知道,就在那一年,日本人要来了。她也不知道,自己后来人生中的许多际遇与转折、遗憾与不甘,都是从那一年开始的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,红军来到沂蒙山,号召青年参军入伍,上火线打鬼子。红军文工团在县城各处街头表演歌唱,唱了三天,曲目没有重样的,姑娘小伙儿都特别精神,这大阵仗吸引了无数山里人前来。
大小姐挤在汹涌的人潮中听了三天。第四天,她想都没想就跟着部队走了,还带走了自己的妹妹。
多年后,大小姐曾对我的姥爷说起过她毅然参军的原因:红军文工团的姑娘们抛头露脸,张嘴就开唱,挺起胸脯、昂起头、伸开双臂就摆出向着炮火前进的英雄姿势,当时她感觉眼前打开了一扇门,门外就是崭新的世界。在那个世界里,可以自由歌唱,心也是自由的,可以随着歌声飞到云霄里去,让人很想跟着歌声一直走。虽然那些姑娘没自己唱得好听,但大小姐头一次觉得,自己就应该这样活,走出小院,走出小村,走出大山,看看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。她的念头变成了决定,她要加入大部队,跟着姑娘们唱歌,给战友鼓劲,唱着唱着,“土改”就会成功的;唱着唱着,就冲上杀敌的线;唱着唱着,鬼子就全都能被赶出中华大地。
队伍从山东行军到安徽。一次,鬼子夜袭,战友们殊死抵抗,伤亡惨重。第二天战火平静后,大小姐坐在土坡上,战友们无力地靠在树上或趴在地上,神情沉郁呆滞。大小姐站起身,高声唱起家乡的民歌《沂蒙山小调》:
人人那个都说哎,沂蒙山好啊。
沂蒙那个山上哎,好风光啊。
青山那个绿水哎,多好看啊。
风吹草低哎,见牛羊啊。
听到乡音,家在山东的战友们都落了泪。泪水冲刷着脸上厚厚的尘土,留下两道小沟般的痕迹。不知道大小姐是否在那一刻成熟了起来,她更加坚定地确信,自己的人生就应该与歌声、战争、革命连在一起。但我相信,一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她的内心深处生发开来,哪怕所有人都倒下了,她也要在这力量的支撑下站得直直的,唱着歌鼓舞战友把鬼子打跑,唱着歌回到家乡沂蒙山。
意想不到,半个月后大小姐真的回到了沂蒙山。年幼的妹妹熬不过风餐露宿、日夜行军,得了结核病,大小姐不得不把她送回家。但她没有想到,这一离开就是永远。当她安顿好妹妹,嘱咐好母亲,想要重回大部队的时候,队伍早已开拔,她怎么也联系不上战友们,掉了队。
那时日本鬼子早已包围了山东,隔三差五就来扫荡,杀戮平民、奸淫妇女。一有风声,大小姐的母亲便跑到厨房灶台底下抓两把炉灰抹在两个女儿的脸上,把她们扮成傻子,以免遭受践踏。鬼子的扫荡越来越频繁,母亲身单力弱,这样东躲西藏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她只能想到后一个办法,便托了媒人,把大小姐赶紧嫁出去。兵荒马乱的年月,就连媒人都没见过新郎的面,只不过走进新郎家的小屋,用手摸了摸墙壁,感觉还算光滑,便知道是家境过得去的人家。回来一说,大小姐母亲连忙答应,不容大小姐争辩,也没来得及选黄道吉日,更没啥嫁妆,走了几十里山路,含着泪把她送到了夫家。
命运又一次剧变,对世事懵懂无知的她,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门外的天地,就又被关进了门。她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妻子,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家。婚后,她很快生了好几个孩子。家里的活儿,她根本不会干却要面对,一大堆家事、柴米油盐让她越来越心烦。她和丈夫从来都没什么话可说,她和孩子们也不那么亲近。
一开始,她还没有死心,渴盼有一天能联系上大部队,重新跟着部队到处打仗。但是日复一日的杳无音信很快让她明白了,这一次,她再也回不了部队,再也不能继续歌唱、打仗了。就好像生活熄灭了后一丝火苗,她的脸上越来越没表情,后似乎都不会笑了。
几年后,大小姐随丈夫投靠早先“闯关东”的姨娘一家,也到了东北。在我姥爷一生的记忆中,无论是关里的山东还是寒冷的塞北,大小姐再也没有开口唱过一首歌。
大小姐选择了沉默,或者是沉默的反抗,哪怕这样的反抗会伤到自己,让日子更加艰难。每天,她都不笑,脸色忧愁地坐在炕沿上,却丝毫不改自己的大小姐姿态。她讨厌劈柴、架火、煮饭,能不干就不干。她一辈子从未下地干过农活,丈夫为此与她日日争吵甚至大打出手,她依旧倔强沉默地坐着。她的性情很古怪,她厌极了鸡鸭鹅狗猫这样的活物,一辈子也没养过一只。她家的院子总是冷冷清清,堂屋也没啥客人。她和孩子们虽不亲近,却也偶尔将好吃的食物攒起来给他们,这让孩子们有点惶恐又有点欢喜。她和母亲不怎么来往,却常常把妹妹接来照应。农妇那些粗俗泼辣劲儿,她是万万没有的——她是大小姐,她的说话和做派,永远和身边所有人都不一样。
“文革”时候大小姐四十多岁,已经有了四个孩子。大小姐居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,因为她家的土地在“土改”时都被充公,她的身份彻底变成了贫农。
说到这里,姥爷已经老泪纵横。也许只有他知道,他的母亲,那位没落的贵族,看起来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大小姐,默默咽下了多少苦。
我不禁感喟,繁华旧事,苦难前尘,大小姐看不到出路,走不出自家的院子,关闭了心门。她保持着大小姐高贵的尊严感,哪怕一生都消耗在执拗与冷漠中,被多少懊悔与不甘折磨。大小姐的做派,是对自我多么痛楚的坚守,对命运多么直接又百感交集的反抗。她是如此坚持,遥望着曾经的梦想,直到人生的终点。
大小姐的后岁月,应该是继她参军岁月后热闹非凡的一段时光。
那时她卧病在床,全家人轮流陪伴在床前,给她削水果,喂她吃罐头。那时的我依旧有些讨厌她,极不情愿地拿本《中国神话故事集》念给她听。而她总是望向天空,依旧是不笑的。
突然一天,她说她想要个金戒指。妈妈立即去商场给她买了金戒指、金耳环,我们给她戴上,她的表情似乎很复杂,想笑又笑不出来。她一动不动,一直端详着手上的戒指。弥留之际,她目光散乱,使了好大的劲儿,才在嘴角绽放出一丝浅浅的笑,轻轻地对我们说:“你们看,这‘金手表’,多好看啊。”也许,她又想起了爷爷把她抱在怀里,
给她好多金银小物件的情景。她是否又想起自己苦涩的命运之路,曾有机会开怀歌唱,为了理想跨越千山万水,而后无奈地品尝了那么多年遗憾与伤悲的滋味。那个时代,是否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大小姐呢?
此刻,我站在她曾住过的院门前,望着远处的高山。多年之前,大小姐是否也曾站在这里眺望远方,想起她那些战友,怀念起那些逝去的生命,想再唱唱那些战场上的歌?也许远方偶尔传来枪响,她会心中一惊,上前几步焦急地观望,以为她的队伍回来了,她就能再续前梦,过上艰苦而热烈的革命生活。
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说:“我们看似可以掌握时代的命运,但说到底,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。”
儿时的我,没有尝过生活的苦,所以那么不喜欢大小姐;如今的我,品味了生活的轻愁,再看大小姐的一生才体会到一个年轻人的“少年不识愁滋味,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人生是苦,心里的苦更苦。我还没有资格说苦,也懊悔自己懂得太迟,没有以孩童的纯良对待她,和她美好地相处,给她一些爱和欢笑。
那个永远要自己吃喝完毕才荫及下人的大小姐啊,那个想要别人赞美她发型好看,整日严肃却在听到几个孩子胡乱歌唱后突然笑起来的大小姐啊,你在另一个世界,有没有赶上你的革命队伍?你是不是又站在山野的土坡上,唱起《沂蒙山小调》?你是不是自己做主选了前路和远方,之后笑容满面地过着想过的日子?
当晚,我做了个梦,梦里的大小姐面容美丽,眼角虽然还有一丝高傲,一丝哀愁,却在无比热烈地高声歌唱。
大小姐,我姥爷的母亲,按东北的习惯,我该叫她“太奶”。
| ISBN | 978-7-5086-8053-8 |
|---|
相关产品
-
猜猜这是谁的屁股呀?-水里的屁股
DKK 59,00原价为:DKK 59,00。DKK 50,00当前价格为:DKK 50,00。 -
猜猜这是谁的屁股呀?-昆虫的屁股
DKK 59,00原价为:DKK 59,00。DKK 50,00当前价格为:DKK 50,00。 -
谁吃了我的苹果?
DKK 68,00原价为:DKK 68,00。DKK 50,00当前价格为:DKK 50,00。 -
谁藏起来了
DKK 49,00原价为:DKK 49,00。DKK 20,00当前价格为:DKK 20,00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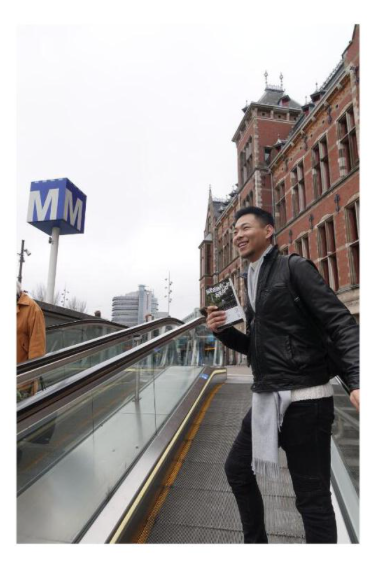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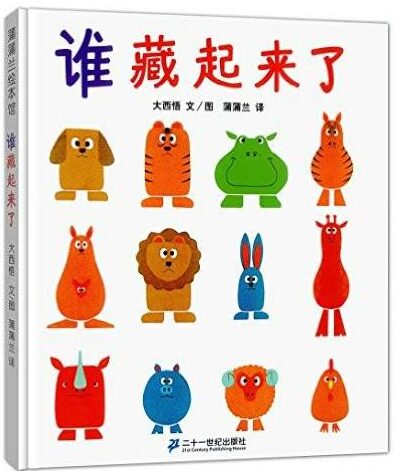



评价
目前还没有评价